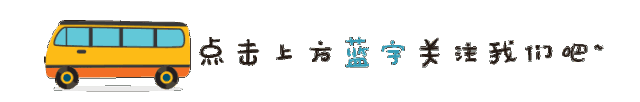

传统马来社会以马来王权为认同中心,并以伊斯兰法和马来传统习俗诠释和制约其社会规范。英国全面殖民马来亚时期(1874-1957),伊斯兰法被分解成穆斯林的私法或属人法(personal law),大幅降级为个人家庭或民俗事务的法律,成为英国普通法(common law)体系的一部分。在保障宗教自由的前提下,马来西亚之前身——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时立伊斯兰为官方宗教。依据马来西亚《联邦宪法》,马来族群都是伊斯兰教教徒,所以支持伊斯兰教的活动可以说就是支持马来族群的活动。马来西亚独立后延续伊斯兰法院的体制,其意义除了作为马来主权和马来王权的象征之外,其主要的功能是为了捍卫马来人传统文化的完整性,以及维持马来人领导的国家体制。宪法也为此订下了一条马来族群认同的“权威教条”,并将他们从其他族群中加以分离,使之成为一个独特的政治社群以和非马来人作区隔,并赋予他们优越地位。马来西亚独立时在其宪法中赋予伊斯兰教3项主要的优势地位:其一,国家有责任资助一切和伊斯兰教仪式、教育、福利有关的机构;其二,宪法赋予各州立法禁止其他宗教信徒向伊斯兰教信徒传教的权力,以维护伊斯兰教信仰人口;其三,各州拥有伊斯兰法院,以规范穆斯林的信仰事务和家庭事务。因此自建国以来,马来西亚穆斯林和非穆林各自在私法和家庭事务上,受制于不同规范,有相互并存的两元法律体系(dual legal system)。惟伊斯兰教为马来西亚的国家宗教并不代表它是依据伊斯兰教理念而创建的国家,伊斯兰法的权力基本上属于家庭法和私法的范围,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也数次公开宣示马来西亚是一个世俗化国家。在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初期,制宪者的理念、开国先贤的态度、君主立宪制中君主的权威以及司法体系的约束都适当地阻止了伊斯兰教对马来西亚政治活动和公共事务的介入。因各种制衡机制的存在,伊斯兰教作为国家宗教在建国初期独立于一般政治纷扰,宗教与政治维持着适当的分离。
马哈蒂尔(Mahathir bin Mohamad)统治时期(1981-2003)通过实施大规模的伊斯兰化政策和伊斯兰法律体制的改革,大举提高了伊斯兰教的地位,这段期间马来西亚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法律方面的伊斯兰化政策,近20年来马来西亚司法机构也正逐渐扩大解释伊斯兰教作为马来西亚联邦宗教的含义,伊斯兰教的地位在多次的法律判决中也不断得到提升,使其逐渐脱离最初的设计。这个时期伊斯兰法律改革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以伊斯兰价值制定一般的行政命令或法律,以及对伊斯兰法律体制进行扩权。其中伊斯兰法律体制的扩权包括(一)1988年大幅提升了伊斯兰法院的地位,使联邦法院对伊斯兰法院的判决不再拥有干涉的权力,伊斯兰法院的判决由过去可以被民事法院推翻的弱势地位,提升至拥有独立法权的地位。同时,自1988年起伊斯兰法院也拥有逮捕人的权力,这对马来西亚伊斯兰法律体制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二)伊斯兰法律组织扩大。在执政党巫统(UMNO)的主导下,自20世纪90年代,各州伊斯兰法院陆续成为独立于各州伊斯兰教理事会的组织,由一院制改为三院制;伊斯兰法院开始有专属的办公大楼,不再与民事法庭共享一庭;各州伊斯兰教理事会的预算大幅增加,州伊斯兰教局的“执法警力”也有很大的提升,监督穆斯林诸如饮酒、男女亲密行为等不法行为。(三)伊斯兰法规范的事项增多,包括惩罚限度的提高和规范罪行的增多。1984年,伊斯兰法院的惩罚限度提高后,各州陆续制定专门的伊斯兰刑法,更首次将“男女幽会”或“亲密行为”纳入罪行,对国内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形成更加严密的规范,让马来社会更趋于保守,也逐渐改变了全国的社会面貌,导致原本马来人领导的国家体制进一步向伊斯兰领导的体制倾斜。
马哈蒂尔执政时代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法律体制已突破过去聊备一格的地位,英殖民时代只是为保留苏丹象征性权力而设计的伊斯兰法律体制,在这时期一举成为掌有实权,且可以和世俗法律体系相抗衡的法律单位。当初,为避免马来西亚出现伊斯兰领导体制,制宪者将伊斯兰教事务分解为各州的自治权力,并明确指明其是属于君主的权力。基于君主立宪制下君主不能干政的传统,伊斯兰教事实上被宪法圈禁在一个窄小的范围内,无法对国家的治理发挥领导作用。但马哈蒂尔时代打破了这一平衡。这场规模庞大的法律改革源于马哈蒂尔这位史无前例的威权领袖和一个日渐集权的中央政府。1969年后巫统通过收编众多的小党,组成国民阵线(Barisan National,BN)联盟,建立起一党独大的政体。1969-2008年,国阵联盟不仅以2/3以上的席次牢牢控制联邦国会,而且长期稳定地在除吉兰丹以外的马来西亚各州执政,这使各州的州议会能遵照中央政府的改革方案立法,变更各州的伊斯兰法律体制。因此不仅伊斯兰法律体制改革能快速地进行,掌控中央行政权的首相署也快速扩张其管控伊斯兰教事务的职能。其结果就是马来西亚向“现代伊斯兰国家”的目标奔去。
但也就在马哈蒂尔时期,马来西亚伊斯兰激进主义崛起,逐渐动摇马来西亚的政体。期间,作为制衡力量的非穆斯林反对党,司法权和马来苏丹的权力皆受到很大弱化。此时,巫统交互利用马来人的民族意识和伊斯兰主义来凝聚支持,逐渐摆脱王权的束缚,全面巩固其一党独大的政权。马哈蒂尔政府的联邦行政机构介入甚至主导伊斯兰教事务,伊斯兰教因此成为执政党建构伊斯兰领导体制的工具。马哈蒂尔时期造就了巫统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威权统治,宗教事务已不再完全为马来苏丹所掌控。2001年9月29日,马哈蒂尔在事先没有征询苏丹任何意见的情况下,宣布马来西亚是伊斯兰国家。至此,马来西亚伊斯兰教政策的决策体系已经演变为巫统内部领导精英专断的决策体系,世俗的统治权力对伊斯兰教实施更深入的影响。巫统不断利用伊斯兰教的语言,师法宗教激进主义政党,将人民对信仰的顺从转化为对统治权力的顺从,并合理化对异议和弱势的压制。通过实施这种策略,加之目前四分五裂的反对党制衡不力,巫统的政权看似更加稳固。但从长期而言,实施日渐保守的伊斯兰化规范,会使宗教激进主义逐渐发展成为普及马来社会的意识形态,巫统终将受制于伊斯兰化的草根力量,遭受伊斯兰激进分子反噬。为今之计,马来苏丹、巫统开明的政党领袖和元老、誓言维护世俗体制的反对党、国阵其他成员党以及司法官僚和知识分子,成为防止马来西亚国家政体进一步变化的最后一道防线。
(摘编自《南洋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
转载自“南洋问题研究”微信公众号
马来西亚研究资讯Informasi Pengajian Malaysia 爱生活@爱大马
 最及时的大马学术信息长按,识别二维码,加关注
最及时的大马学术信息长按,识别二维码,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