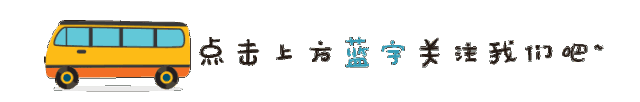

回顾513历史事件时,经常只沦为“大写的历史”(History),罹难者只剩下一组数字,面孔模糊不清、没有姓名。50年后,这个历史创伤仍是个禁忌话题,仍在世的罹难家属经常活在恐惧的阴影下。他们明明最靠近这段历史,却往往成为最失语的一群。
罹难家属经历生命的剧变后,究竟如何走过后来的人生?他们痛失的亲属好友当初又经历了哪些事?
吉隆坡甘榜巴鲁希律(Jalan Hale,今已更名Jalan Raja Abdullah)曾有一户黄姓大家庭,10名家人中,有5人在暴乱中遇难丧生。
1969年513事件爆发时,黄大姐是一个24岁的女孩。离家出外工作的她,就在一夜之间痛失5名家人,包括74岁的祖母、50岁的母亲、18岁的妹妹,还有两名分别14岁和10岁的弟弟。
“关于这段记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敢想、不敢提、不敢问,因为我很痛苦。”
转眼间,黄大姐也年届74。她至今都还不知道她的亲人葬身何处,50年来也没有机会拜祭他们。
黄大姐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低头掩面痛哭,半分钟后,情绪才平复过来,“我真的很想把我遇难的家人都通通忘记,可是我不敢忘记。如果连我都忘了他们,还有谁会去记得?”
513事件的罹难人数众多,大部分非穆斯林死者最后葬在雪州双溪毛糯(Sungai Buloh)的墓园, 而穆斯林死者则葬于雪州鹅唛(Gombak)。根据官方报告,只有8具罹难者尸体归还亲属安葬,其余皆由政府处理。
亲人在暴乱中丧生,家属未必有机会送他们最后一程,不少罹难者的身份无从识别,因此葬身在双溪毛糯墓园的多个墓碑上,写着“无名氏”(unidentified chinese)。
“这起事件发生后,一直没有人来给我们一个说法或交代。我们只能一直哭一直哭,然后,生活慢慢恢复正常。其实,我们家属内心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缺失,我们少了一个了结。”
“……现在,我鼓起勇气将我家里的事情说出来,是因为我要让大家知道暴力的可怕,我要让大家知道我的痛苦,我要让大家记得我的家人。唯有当大众都开始去记得历史,作为遇难者家人的我们才能放心忘记他们、放下过去。“
以下是黄大姐对513事件的记忆:
我已经不记得我是否有在1969年投票。当时,我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我相信,我的其他家人也是如此,否则他们不会对家门外酝酿中的动乱一无所知,最后遭围困而死。
我们是一个典型的底层家庭,一家十口住在希律一间租来的平房。513事件爆发时,我们几个大的孩子都在外头工作,这也是我们都活下来的原因。
513那一天,我人在适耕庄,同事们还觉得高兴,“啊,戒严了,我们可以几天不用上班啦。”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吉隆坡发生什么事。

513骚乱后,黄家被烧成废墟。图为黄家同排房屋的情景,摄于513事件次日,由动画工作者哈山(Hassan Muthalib)拍摄和提供。他的住家与黄家相距仅50米。513事件次日,他拍下黄家同排房屋的情景。
几天后,通讯终于恢复。我弟弟从吉隆坡打电话来告诉我,留在家里的5个家人全部失去音讯,顿时让我觉得晴天霹雳。
解严后,我顾不上危险,顾不上同事的阻拦,忐忑不安地乘的士到巴生的姑姑家,和其他幸存的兄弟姐妹会合。从巴生,我们5个兄弟姐妹再想办法来到吉隆坡。
到了吉隆坡,从警察局到医院,我们像盲头苍蝇,到处都找过。“到底我们的家人在那里?为什么他们不联系我们?”
废墟中的一具遗骸
事发大约10天后,吉隆坡市中心终于解严了。我们总算可以回家了。
回到本来是住家的现场,我什么都不认得。整排房子烧掉了,一切面目全非。空气中浓烈的尸臭味,我忍不住蹲下来呕吐。
废墟中,我约莫认出了我们客厅的模样,也看到了一具上半身只剩下骷髅骨的遗骸。谁?是谁?
“阿川,是阿川啊!”从遗骸脚上穿着的鞋子,我认出来了,那是我14岁的弟弟晴川的腿!
一时间,我只懂得蹲在地上痛哭。阿川是我们黄家最优秀的孩子,本来是我们全家的光荣和希望,但是他竟然死了!
华人用万箭穿心、肝肠寸断来形容心灵创痛。惟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这是多么贴切的说法。这么多年后,我还记得当初那种的痛楚。
其他兄弟在废墟里找到晴川的二胡,还问我要不要捡起来。我万念俱灰,告诉他们:“以后睹物思人,看到就伤心,这种东西通通不要了”。
后来,我真的很后悔。虽然我完全不想看、不想提513事件,但是我还是认为,当初应该把那把二胡留下,当作一个纪念。

黄家原本一家10口,其中5人在513事件中遇难(见图)。左起为妹妹黄毓秀(18岁)、弟弟黄晴川(14岁)、祖母林氏(74岁)、母亲陈美月(50岁)和弟弟黄浩然(10岁),弟妹皆为吉隆坡中华中小学学生。
只有祖母的遗容“最干净”
我不停不停地在哭,脑袋空白一片。后来的许多事情,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只约莫知道,大哥去了谐街(Jalan Tun HS Lee)的警察局,看照片认出了其他3个家人。他们都遇难了 。
大哥说,所有人里,只有我祖母的遗容“最干净”。其他二人的死状到底如何,他没有说,我们也没问。
警察告诉我大哥,罹难者的遗体都葬在双溪毛糯。到底在双溪毛糯的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剩下的几个兄弟姐妹,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寻找坟墓。几十年来的清明节,我们从来不曾拜祭。事实是,513事件之后的几十年里,我们都绝口不提513。就算偶尔提到,大家都很有默契地马上转移话题。
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共有的最大伤口,没有人敢去触碰。后来,我孩子出来工作后,说要替我找他们的坟墓,我也拒绝了。
什么祭拜、什么仪式都是假的。找到了墓碑又能怎样?拜祭了又能怎样?难道他们能够死而复活吗?
“为何死的那个不是我?”
513事件后,我曾经一直问自己:“为什么死的那个不是我?”如果我死了,至少我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会明白那种撕心裂肺的痛。
不知道有多少个晚上,我不能睡觉。不知道有多少次,我都难过得想去死。只要白天一提起这件事,我就会整个晚上不能合眼,觉得日子过不下去。
所以,关于513事件的回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敢想、不敢提、不敢问,因为我会很痛苦。大火也把我们家的照片烧个精光。
因为一直不敢去回想,很多年后我才突然发现,原来我已经想不起我妈妈长什么样子。甚至,我的祖母、我的两个弟弟和那个妹妹,他们的面目都非常模糊。为什么我会把他们忘记了?
其实,我真的很想把他们都通通忘记,可是我不敢忘记。如果连我都忘了他们,还有谁会去记得?

图为黄大姐祖母的死亡证,死因注明为“砍杀”(KENA TETAK)。
后来我结婚有了孩子后,偶尔和子女一起去小旅行时,都会想起我那个苦命的妈妈。我总在想:“如果我当时也能带上我妈妈,和她一起旅行就好了。”
我妈妈一生劳碌,结婚生子后,困在希律的那间小房子里照顾一家大小十几口,连离家远一点的地方都没去过。如果没有发生513事件,再过几年我的弟妹很快都会毕业出来工作,她就可以过上好一点的日子了。
可惜,她一直没有等到那一天的到来。
我那3个遇难的弟妹,性格比较木讷文静,但全部都是能读书的小孩。
我的妹妹毓秀遇害当年只有18岁,在吉隆坡中华独中就读高三,正值豆蔻年华。关于当晚的情景我耳闻许多,但一直不敢去想象,在那么多暴徒包围的情况下,她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到底遭遇了怎样的折磨。她的命运一定很悲惨。

图为黄晴川来不及领取的奖杯,1969年遇难后,由姐姐于同年年底到校上台代领。
晴川来不及领的奖杯
我和最小两个弟弟的年龄差距比较大,分别比他们大10年和14年。我们的父亲早逝,很早就成为没有爸爸的小孩,而且家里又很穷,所以我特别疼惜他们。
晴川死时只有14岁。他的死也最让我痛心。他个性腼腆安静,是一个十项全能的优异学生。当年我们家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去特别栽培他,但是他却样样无师自通。三语演讲、作文、书法、篮球、唱歌、二胡、绘画,他样样精通。每次考试和比赛,他都拿第一。
1969年底,我妹妹哭着去中华国中的校园颁奖礼,上台替晴川领了3个奖。那是他在1969年遇难前几个月在学校赢得的奖项,分别是篮球比赛冠军、英语演讲比赛冠军、华语演讲比赛冠军。
他以前赢得许许多多的奖牌,全部都在513骚乱中被烧光了。他是一个那么难得的人才,如果当年没有遇害,日后必定大有作为。

图中前排左一为黄晴川,照片原摄于1968年,是家人后来向其同学借来,到摄影馆翻拍且仅存的惟一影像;右侧是黄晴川的画作以及撰写于1968年的作文,题为《我的家庭》。
我最小的弟弟是黄浩然,患有小儿麻痹症,自小就瘸了一只脚。他4岁就没了父亲,大家都很怜悯他,也是家中最得宠的小弟弟。
小时候,我会让他坐在我大腿上,把他抱在怀里亲亲他,嗅嗅他的乳臭味。在适耕庄时,我还会写信回家给他。信里头一半是文字、一半是图画,鼓励他要好好听家人的话,谁知他却始终无缘长大。
从小我就和目不识丁的老祖母同睡一间房,一直到我19岁离家外出工作为止。每天晚上,我都听她絮絮地说着她家乡的故事,摸着她冰凉发皱的手臂入睡。
我的祖母不杀生,持素了几十年,每天在家都披着袈裟敲木鱼、拜佛念经。她那么瘦弱,暴乱当晚暴徒只要推她倒在地上,她就没有了。
他们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我经常设想,他们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到底有多惊恐、多无助?他们5个人,老的老,小的小,全都是老弱妇孺;他们一点杀伤力都没有,也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513事件发生时,我们活下来的几个兄弟姐妹都非常年轻,最大的27岁,最小的才17岁。全部人都手足无措。没有人教我们应该怎么办,只懂得一直不停地哭,连续哭了好几个月。
我们的家当全部烧毁了,长辈和弟妹也死掉了,我们名副其实地“家破人亡”。后来,政府安排我们入住敦拉萨路17楼组屋,但是我们各自在不同地点工作,5人中只有两人常住那里。
从此以后,我们就再没有“回家”的概念。我们的家散了。

黄大姐和黄浩然的合照,约摄于1964年;右侧为黄浩然四年级时的音乐课本,以及在另一课本的涂鸦。
冀设立纪念碑悼念遇难者
当年干下这些暴行的暴徒,我相信还有很多仍然在世。我不知道这些年来,他们会不会良心过意不去、会不会忏悔?为什么他们那一刻可以那么残忍?
以前,我们家对面就是马来甘榜,我们和这些马来邻居虽然不相往来,但是却相安无事,相处和谐。我始终相信,513暴动是有组织的外来群众行凶事件。我不能相信,我的马来邻居会杀害我的家人。
这起事件发生后,一直没有人来给我们一个说法或交代,我们只能一直哭一直哭,然后生活慢慢恢复正常。其实,我们家属内心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缺失,我们少了一个了结。
总有一天,得有人给这些罹难者一个公道,要给家属一个交待。即使我有生之年看不到,我也希望我的下一代能得到答案。
我希望有关当局能够立一个纪念碑或纪念馆,把受害者的名字和生平刻在上面,让世人知道,一个10岁的孩子,没有理由要承担这样的罪过。
我要让后世的人知道,他们是多么地无辜和冤枉。我希望,历史永远永远不要重演。
其实,我一直都不愿意提起这段往事。现在,我鼓起勇气将家里的事情说出来,是因为我要让大家知道暴力的可怕,我要让大家知道我的痛苦,我要让大家记得我的家人。
惟有当大众都开始去记得历史,作为遇难者家人的我们,才能放心忘记他们、放下过去。
(原载《当今大马》2019年5月14日)
马来西亚研究资讯Informasi Pengajian Malaysia 爱生活@爱大马
 最及时的大马学术信息长按,识别二维码,加关注
最及时的大马学术信息长按,识别二维码,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