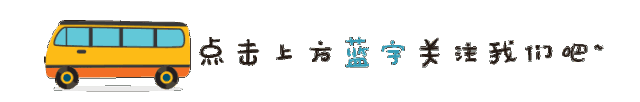
01
前 言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境内或跨境、跨域乃至跨国的人口流动与移民,是从古至今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普遍现象。而与人口移动相伴随的,则是由移民带来的不同文化在移居地的传播与移植。因此,当外来移民在新土地上重建家园,这些源自移民原乡的文化亦要在新的时空情境下转变轨迹,逐渐发展成为在地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诸多的矛盾、碰撞、冲突,甚至引发战争,但文化间的交流、互动、融合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而其最终的结果则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的发展。有鉴于此,当进行移民尤其是跨境跨国移民课题的研究时,即要考察看的见的人的移动,亦要关注看不见的文化的移动、即因移民而产生的文化传播与移植、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形态的文化互动与新文化的出现对人类文明与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
东南亚是海外华人最主要的聚居之区。地处东南亚的新加坡,其人口中有三分之二以上为华族,是大中华以外唯一一个以华人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并非当地土著,他们的祖先主要是在鸦片战争后一百年从华南来到南洋拓荒的中国移民,由他们带来的华南原乡文化也随之传播并移植到这片新土地上。在不同于祖籍地的时空脉络下,华南移民伴随东南亚的历史演化在当地落地生根,该地区也因此成为中华文化在海外创造性传承与发展的一个重镇。
本书正是基于上述学术理念与对东南亚华人社会文化的认知而展开对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的研究。所谓“宗乡文化”,是指源自中国华南地域的传统民间乡土文化、在新加坡从殖民地时代到本土社会的时空变迁中、伴随华人社会的建构与演化的历史进程而发展起来的、作为华人文化乃至新加坡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形态。
在中国传统典籍里,“宗”与“乡”是两个概念。“宗”最基本的意涵是指“祖庙”、“同祖”、“同族”。“乡”最初是因周代建制以一万二千五百户为一乡而指古代的一种居民组织,其后逐渐演化,泛指城市以外的农村地区,也引申为出生地或家乡。可见,“宗”与“乡”的原意,前者与宗亲血缘相关,后者则与乡亲地缘相连。而结合“宗”“乡”形成 “宗乡”概念、以及由此概念形成的社团形态“宗乡社团”,则出现在当代新加坡华人社会。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新加坡政府为因应内外形势的变迁,鼓励国内的华族、马来、印度等各种族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与传统习俗。在此背景下,新加坡政府官员相继走入华人社团展开工作。1979年时任劳工部政务部长的谢嘉惠参加惠安公会三庆大典。他在致辞中,促请宗乡会馆开放门户吸纳年轻人,扩大服务,以适应新的时代。这是笔者所见新加坡传统华人社团被称之为“宗乡社团”的最早记录。到了1984年,当时正是新加坡全国大选前夕,政府部长纷纷走访各选区。时任不管部长后成为总统的王鼎昌来到华人社团聚集的社区访问。他亦以“宗乡社团”统称会馆、同乡会、宗亲会等,鼓励这些建立于殖民地时代的华人团体与时俱进,在新的时代重新找到社会定位。
政府的鼓励与推动得到当时正在寻求生存与发展契机的华人社团的积极响应。在与王鼎昌部长的对话中,时任新加坡晋江会馆会长的蔡锦崧提出,政府应重视民间社团的力量,尤其是应与宗乡会馆保持密切联系。“因为宗乡会馆在保留与发展传统文化方面可扮演重要角色”。这是新加坡华人社团领袖首次以“宗乡会馆”自称。在这次对话后,围绕着宗乡会馆如何在新时代转型与重振等问题,新加坡华社展开一系列讨论。1984年12月2日由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广东会馆、福州会馆、南洋客属总会、琼州会馆、三江会馆及惠安公会等社团联合发起、在潮州会馆举办主题为“我国宗乡社团如何在新时代扮演更积极角色”的“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来自全新加坡的185个华人社团的665名代表及其他35个社团代表及个人出席了此次大会。在研讨会上,王鼎昌代表政府肯定华人宗乡社团对新加坡社会发展的贡献,并提出促使会馆在未来转型与发展的五点建议。经过激烈的讨论与辩论,研讨会在总结时提出对未来发展的十大建议,其中包括“尽速成立全国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以便统筹与协调各会馆今后的发展与合作”等内容。1985年1月23日,已经升任副总理的王鼎昌再次邀约各大方言社群的主席共进午餐,希望大家为了会馆的前途和华社的利益,务必支持并尽快成立全国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他特别指出,总会的成立有助于推广华文华语及中华传统文化,并建议由福建会馆主席领导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85年2月7日,福建会馆主席黄祖耀召开记者会,宣布全国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即将成立。经过近一年的筹备,总会于1985年12月9日获准注册。1986年1月29日,“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以下简称“宗乡总会”)在香格里拉酒店大厅举办隆重的成立大典。至此,由政府直接推动的、在当代扮演整合传统华人社团功能的宗乡总会正式出现在新加坡华人社会舞台。与此同时,“宗乡文化”、“宗乡社团”等从此成为当代新加坡社会约定俗成、称呼建立于殖民地时代的华人社团与传承自华南民间的华人传统文化的话语。
从以上阐述可见,虽然“宗乡”与 “宗乡团体”的称法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出现,但从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血缘宗亲”与“地缘乡亲”关系是伴随闽粤移民而来的“文化移植”。而“宗乡团体”则是运用这些传承自华南传统民间社会的“宗”、“乡”文化资源而建立会馆、同乡会、宗亲会等的华人社团组织。正如新加坡历史学者、资深报人彭松涛先生所言,“所谓‘宗’即同姓、同宗、血缘关系,‘乡’即同里、同乡、地缘关系。宗乡组织即血缘加地缘的组织”。作为华人社会基本的组织架构,这些社团形态早在殖民地时代就普遍存在于东南亚各华人社会。根据吴华的《新加坡会馆志》,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在新加坡建国之前建立、保留下来的的会馆、宗亲会、行业公会等华人社团仍有五、六百所之多。而在马来西亚,根据1999年的统计,当年全马有五千多个华人社团。
另一方面,“宗乡文化”与“宗乡社团”名称的出现,亦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社会变迁的产物。众所周知,在半自治殖民地时代建立、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社团,扮演华人社会“政府”的角色,不仅是维持那一时代华人社会运作的组织机构,亦是中华文化在东南亚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华人社团的这些特点,尤其是承载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功能,符合新加坡政府鼓励各种族保留传统文化的政策需求。有鉴于此,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政府借助“宗乡”话语与对“宗乡文化”的强调,由上而下重新整合并推动在建国后不断被边缘化、且在民间社会仍拥有较强实力的华人传统社团转型,使其承担保留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与价值观之功能。而基于自身与华南原乡一脉相承的文化内涵与生存需求,华人社团也认可并接受政府的提法。
总括以上所述,在文化内涵与组织形态上,“宗乡文化”与“宗乡社团”,等同于殖民地时代即已普遍存在于东南亚的华人文化与社团形态。然而,在当代新加坡语境下,二者在社会功能上还是有差异。从殖民地时代作为新加坡华人社会三大支柱之一的“华人社团”、到新加坡建国之后、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成为保留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宗乡社团”,客观上反映了华人社会在新加坡时空变迁脉络下的变迁与演化。
2002年笔者在一项有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蓬勃兴起的海外华人社团世界恳亲联谊活动的研究中,首次以“宗乡文化”为理论框架,讨论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时空情境下,海外华人社团的认同形态与跨国网络。在这项研究中,笔者从维系海外华人社团内在文化纽带的视角,对“宗乡文化”所涉及的内容与功能等诸方面进行初步探讨。笔者认为,遍布世界各地、差异性很大的华人社团之间存在着一条被称之为“乡情”、“乡谊”的血脉相连的共同文化纽带,那就是对“宗乡文化”的认同。所谓“宗乡文化”,涵盖了祖籍地与移居地两方面的内容。在祖籍地方面,主要指方言、宗族观念、祖先崇拜、神明信仰、节庆习俗等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内容与形态。“宗乡文化”的另一层内容,则是海外华人运用传承自祖籍地的传统民间文化资源,在移居地建构与发展的社会文化形态。正因为“宗乡文化”涵盖了祖籍地与移居地两方面的内容,才能成为海外华人社团共有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资源,因而能够承担起为当代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提供文化纽带的重要功能。这是我对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海外华人宗乡文化的最初思考。自此以后,笔者在原有学术积累的基础上,继续以新加坡华人社会为主要考察对象,展开东南亚华人宗乡文化研究。本书收录的内容,是笔者自21世纪初以来研究的心得之作。
本书的正文,以三卷篇幅讨论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宗乡社团”、“帮群坟山”“庙宇组织”与“传统节庆”等。基于新加坡地处东南亚区域、新加坡华人是东南亚华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本书的卷四以“走出新加坡”为题,收入笔者与东南亚华人社会文化研究方法论、新马华人民间信仰等课题相关的七篇学术论文。本书的附录,涉及碑文撰写、书序、书评等项内容,是笔者表述学术理念的另一书写方式。
上述内容的共同主题,在于透过对近现代华南移民运用传承自祖籍原乡的传统民间文化资源、在移居地的新土上再建新家园历史进程的具体考察,研究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承与在新的时空脉络下的创造性发展。以下就本书的内容与主要论点、本研究所运用的华人社会档案资料等各类文献、以及与东南亚中华文化研究相关的思考等问题做一阐述,以期有助于阐明本书的研究理念与基本思路。
02
华人宗乡文化的建构与演化
基于近现代中国的海外移民与南来东南亚拓荒的移民构成,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主要传承自华南地域的传统民间乡土文化。
中国移民南来新加坡,始自1819年新加坡开埠。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与东南亚开发对劳工的大量需求,中国移民持续不断地一波又一波地涌入新加坡,致使本地华人人口不断增加。文献记录显示,从1845年开始,新加坡华人人口已经超出马来、印度等其他种族的移民人数。到了1860年,当地的华人移民已占当时新加坡总人口的61%。这些被称之为“新客”的中国移民主要来自中国华南闽粤地区的破产农民与城市平民等。有鉴于此,伴随闽粤移民而来的文化移植,主要是宋元明清以来在华南地域社会得到长足发展的诸如祖先崇拜、宗族观念、民间信仰、节庆习俗等、以及承载上述内容的闽粤各地不同方言等传统民间文化形态。当这些文化形态在脱离原乡的发展轨迹后,转而进入新加坡的时空脉络,在伴随新加坡华人社会建构与演化的历史进程中,发展成为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
1、从地域文化到社群文化:华人宗乡文化建构
伴随闽粤移民而来的华南地域传统民间文化,是在英殖民统治的移民时代发展成为具有社群边界的华人宗乡文化。制约这一进程的是英殖民政府的统治政策与闽粤移民的社群结构。
英殖民政府统治新加坡时期,采取分而治之与间接统治政策。因此,当大批华南移民来到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拓荒,如何在半自治的殖民地建立华人社会结构与组织形态,是他们面对的共同问题。离开祖籍原乡的华南移民迫切需要文化资源,以实现华人社会的重组与重建。
另一方面,受到移民史等因素的制约,在新加坡开埠初期,华人社会内部即呈现出主要基于祖籍地方言差异而形成的社群结构。来自相同祖籍地说同一方言的闽粤移民往往结合成“帮”,并因操相同方言和具有相同的风俗、习惯等因素,形成各自的帮群认同而与异帮群相区别。在英殖民政府的统治下,这些不同的方言帮群基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的影响,为争取各自的利益,或独立成帮或相互联合,呈现出帮群分立、互动与整合之状态。
在上述两个因素的制约下,承载着祖籍原乡历史、社会、文化记忆的华南传统民间乡土文化在脱离原乡发展轨迹后,即进入新加坡殖民地时代华人移民的社群脉络,承担为闽粤移民的社群整合与社团建立提供文化资源与组织原则的历史新使命,并伴随华人社会的建构而发展出具有社群边界的宗乡文化形态。
本书以具体的个案,重点考察与讨论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闽粤移民如何以源自华南地域传统乡土文化中的闽粤方言、祖先崇拜与民间信仰等作为文化资源,来建立会馆、帮群坟山、庙宇组织等社团形态。
如前所述,制约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社群结构的重要因素,是伴随闽粤移而来的闽南、潮州、广府、客家、琼州等华南各地不同的方言。然而,当这些来自华南各地的方言成为文化资源时,并非简单地运用于华人移民社会,而是历经了一个转换,从在原乡仅具 “语言或文化层次的方言认同”,发展成为一种承载特殊群体意识的“方言群认同”。“方言群认同”的重要功能在于,“当这种意识表现于群体活动时,它便成为一种社群的分类法则”,从而为闽粤移民的社群整合与社团建立提供文化纽带与组织原则。
本书考察了基于“方言群认同”而建立的两类华人社团形态。一类是以移民原乡的祖籍地缘、姓氏血缘等作为认同与文化纽带而建立的会馆、同乡会、宗亲会等。这类社团所要处理与解决的问题,是在移居地的时空环境下,重新确认并界定这些离开祖籍地的闽粤移民的社群所属,进而达到社群重组与整合之目的。
另一类是基于 “帮群”关系建构的社团形态。本书研究的海唇福德祠绿野亭即是一个包括了“广惠肈”、“嘉应五属”、“丰永大”的广府、客家三社群的帮群组织。而广惠肈碧山亭属下则涵盖广府、肇庆、惠州三属的十六所会馆。如果说会馆、同乡会、宗亲会等是基于移民个人的认同意识等而建立,那么,帮群组织所要处理的不仅有本方言社群属下各移民群体的重组,亦涉及华人移民社会内部不同方言社群之间的互动与整合。帮群组织能够提供容纳更多单一华人社群的组织架构与整合机制,其内部的社群关系与认同形态也更为多元与复杂。因此,在华人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伴随“帮”结构的形成与“帮群组织”的建立及制度化,标志着华人移民的社群整合与华人社会建构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建构的历史进程中,祖先崇拜是另一重要文化资源。关于祖先崇拜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传承与“社群化”的祖先崇拜所具有的重要整合功能,本书主要透过闽粤移民建立的坟山组织进行考察。
在殖民地时代的东南亚,坟山组织普遍存在于各地的华人社会。在十九世纪的新加坡,华人移民各帮群都建有坟山与设立坟山管理机构。如福建帮的恒山亭、潮州帮的泰山亭、琼州海南帮的玉山亭、客属嘉应社群的“嘉应五属义山”等。在这些坟山组织中,有一些迄今仍承担社群总机构的功能。例如丰(顺)永(定)大(埔)社群的毓山亭、本书考察广惠肈社群的“广惠肈碧山亭”与广客两帮群的总机构福德祠绿野亭等。
与会馆、宗亲会等社团不同,坟山组织是通过对先人的处理来解决移民生者的社群重组与整合问题。因此,坟山组织具有双重功能,其在作为丧葬机构,处理本社群先人的丧葬与祭祀等事宜的同时,也具有界定不同帮群与促进本帮群内部不同社群整合的重要功能。这显示,第一、坟山组织的内在文化因素是坟山崇拜,而坟山崇拜是中国传统社会祖先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祖先崇拜由此成为闽粤移民在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重建其社会结构重要的文化策略与组织原则之一。第二,经由移民而传播到新加坡的华南的祖先崇拜与坟山崇拜,透过华人帮群坟山组织的建立与运作,已呈现出“社群化”的新形态。
传承自华南的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亦是殖民地时代华人社会建构的重要文化资源。现有的研究已显示,在殖民地时代的东南亚华人移民社会,建庙祭拜移植自华南祖籍地的乡土神明,除了要解决南来拓荒的闽粤移民在新土地上的宗教需求、维系他们的“中国化”与“祖籍认同”之外,有些庙宇还作为移民社群的总机构,承载凝聚与整合社群的重要功能。在新加坡殖民地时代,天福宫曾作为福建移民社群的总机构。粤海清庙、琼州天后宫亦曾是潮州、海南移民社群的总机构。而创办于十九世纪中叶的望海大伯公庙,迄今仍是新加坡“嘉应五属”、“丰顺”、“永定”、“大埔”等“客属八邑”的最高联合机构。以上所述显示,与坟山组织相同,新加坡殖民地时代闽粤移民建立的庙宇组织亦具有双重功能。其在解决华南移民宗教信仰需求的同时,亦为华人社会提供凝聚与整合社群的组织架构。
本书考察的重点,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具体的个案讨论源自华南的传统民间信仰如何在不同于祖籍原乡的时空情境下所历经的“社群化”的发展进程。本书的研究显示,“移神”与“定居”是传统民间信仰社群化的两个重要阶段。所谓“移神”,主要指的是鸦片战争后一百年经闽粤移民的“分香而来的华南乡土神明。而神明的“定居”,则是指所“移”之神在离开原乡轨迹、重新进入华人移民社会后重建的庙宇与神明系统。受制于华人社会的帮群结构,这些“定居”于华人社群的庙宇与神明系统因具有社群边界而呈现出“社群化”特征。这是庙宇组织具有整合所属社群重要功能的奥秘之所在。
总括以上所述,在新加坡殖民地时代,脱离原乡轨迹的华南地域社会传统的“宗”“乡”文化,在新的时空脉络下承担新的历史使命,为闽粤移民在这片新土地上再建家园提供文化资源与组织原则。伴随这一历史进程,其自身也从华南传统民间乡土文化发展成为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
在文化形态上,华南传统民间文化与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的差异在于,前者是地域文化,后者则是社群文化。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变,是透过的华南传统民间文化的“社群化”而实现。在华人宗乡文化的架构下,来自华南移民原乡的福建、潮州、广府、海南、永定、大埔、丰顺等地名,从看得见的地理概念,转变成为看不见的具有特定群体内涵的文化符号。例如,“福建”不仅特指来自同一祖籍地的移民社群,亦作为该群体的认同意识与维系社群的文化纽带。本书所讨论的源自华南的方言、祖先崇拜、民间信仰等,都历经了“社群化”的转变过程。
在文化内容上,为了适应移民时代华人社会整合的需求,源自华南传统民间文化的宗乡文化也有一些发展与变化。以祖先崇拜为例。在移民时代广府、客家等移民帮群设立的坟山组织中,创设了一种在华南原乡所没有的埋葬形态“社团总坟”。“社团总坟”的类别与会馆、同乡会、宗亲会、行业公会等社团形态“阴阳”对应,目的在于建构作为该社群认同象征的“社群共组”,并透过在“清明”与“重阳”期间定期举行“春秋二祭”,来解决移民帮群内部不同社群的凝聚与整合问题。从设立“社团总坟”、建构“社群共组”到制度化的“春秋二祭”,表明基于中国传统血缘性的“亲人”或“亲属关系”在进入东南亚华人移民社会后,朝向虚拟血缘与泛血缘的方向扩大,祖先崇拜与坟山崇拜因而具有了社群边界。相较于华南原乡,社群化的祖先崇拜整合空间更为扩展,不仅具有整合血缘宗族的功能,亦涉及血缘的宗亲团体、虚拟血缘的姓氏组织、地缘性的乡亲组织、业缘性的行业公会等社群组织的凝聚与认同。
综上所述,从地域文化到社群文化,华人宗乡文化所历经的建构进程,既是闽粤移民在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重建其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的产物,亦是华南传统民间乡土文化在海外华人社会创造性发展的结果。
2、社会变迁与华人宗乡文化的当代图像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布独立建国,这是自1819年莱佛士开埠以来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新加坡脱离英殖民政府一个半世纪的统治、进入一个独立、和平、建设与发展的新时期,其人民由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移民转变身份认同成为以新加坡为祖国的公民。在殖民地时代完成建构历程的华人宗乡文化,也随之进入新兴国家的时空脉络。而其继续的演化进程,直接受制于建国后半个世纪新加坡的社会变迁,来自世界区域、包括祖籍地在内的中国等外部世界诸多因素,亦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对具社群属性的华人宗乡文化而言,其自身也面对一个在不同于殖民地时代的国家脉络下转型的问题,即如何跨越社群、朝向作为新加坡国家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方向发展。
(1)制约华人宗乡文化演化的因素
自1965年以来的半个世纪,国家是制约与影响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演化进程的最主要与最重要因素。
关于新加坡建国后半个世纪的社会发展,有学者以1970年代后期为界,将新加坡建国后的发展历程,分成两大阶段,前者为“破”,后者则为“立”。亦有学者将其分成三个阶段:1965年至1985年为“生存的政治”,1985年至2005年为“发展的政治”、从2005至今,则为“整合的政治”。上述分期虽各有其理由,但因其基本符合建国后新加坡社会发展的现实而被学界所认同。在建国初期,新加坡面对的一大挑战,是如何在开埠到建国不到一个半世纪、且基本没有土著与本土文化根源的移民社会的根基上凝聚与塑造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这是关系到这个年轻共和国能否生存的要害问题。为此,新加坡全力运作塑造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受制于种种历史与地缘政治的局限,这一时期新加坡政府的基本做法是置种族认同于国家认同之下,透过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一系列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试图建立超越种族和帮派的社会文化形态,将各种族各族群团结在国家旗帜之下,特别是淡化与抑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族群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以此来强调新加坡人的国民意识与对国家的认同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以后,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东西方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亚太地区出现急剧的社会经济变迁、特别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并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各国恢复或建立正常经贸外交关系。在新加坡国内,1980年代以后,建国历程已趋于稳定,社会经济亦有长足发展。与此同时,建国后二十年推行的以国家认同取代种族认同的政策,虽然有助于促进各种族的凝聚,但也产生不少较为严重的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在这样的内外新形势下,新加坡政府在调整其内政外交政策的同时,强调并积极推行“多元种族多元文化”政策,鼓励各种族在国家认同的前提下,保留与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对于华人族群,自1990年新中建交后,在“搭中国经济顺风车”的政策鼓励下,政府不仅提倡华人社会尤其是宗乡社团举办中华节庆等活动,保留与传承传统中华文化与价值观,亦支持宗乡社团与祖籍地重建联系,在新加坡主办或参与全球海外华人社团的跨国联谊活动。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新加坡社会内部的政治与社会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国家认同的强化与国家文化的建构仍是国家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新世纪之初发生的九、一一事件、巴厘岛大爆炸、以及连续不断的区域极端分子制造的各类事件,使新加坡一直面对来自中东与亚细安等地恐怖主义威胁的严峻形势。有鉴于此,新加坡政府在继续坚持“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国策、积极提倡与推行“种族和谐”政策、强调不同种族间的文化交流与社会融合的同时,鼓励各种族民间社会团体主动承担维护国家种族宗教和谐的重任。
建国后半个世纪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与社会变迁,对华人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
研究显示,从二战后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前,历经二战苦难与黑暗岁月的新加坡华人社会进入发展与转型期。一方面,随着二战后华南移民的再次涌入与本地出生华人人口的增加,华人社会规模不断扩大,在日据时期陷入停顿状态的华人社团也进入了一个重整、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另一方面,基于战后东南亚、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变迁、尤其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所领导的华人争取公民权运动与1965年新加坡的独立建国,促使华人社会进入一个转型期。其主要表现在,二战以前,新加坡华人社会显示较浓厚的移民社会色彩。二战以后到新加坡建国,华人社会本土意识增强,并转变国家与身份认同,成为这个由多元种族组成的新兴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在新加坡建国后二十年的“生存政治”时期,华人社会却因政府推行的“置国家认同于种族人认同之上”政策而陷入民族与文化认同的危机。为了建构新加坡国家认同,政府“合并”(关闭)大中华以外唯一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终结在殖民地时代蓬勃发展的新加坡华文教育体系,从根本上动摇华人社会赖以生存的中华文化根基。宗乡社团是保留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另一重要阵地。而在新加坡政府实施的一系列以国家认同取代种族认同的政策之下,宗乡社团和源自华南传统民间乡土文化、包括方言、节庆、祖先崇拜、民间信仰等诸多内容的宗乡文化因作为对立面而成为牺牲品,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
华人社会发展契机的到来,是伴随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新加坡政府一系列内外政策的调整。这些调整逐步改变建国前期将国家认同与各种族文化认同相对立的社会氛围,从而给华人社会与宗乡文化带来生存与重振的历史契机。
第一、新加坡政府希望华族与华社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与价值观,这些正是华人宗乡文化涉及的主要内容。这就有了本文前言中所提到的政府官员走入华人社会、以“宗乡社团”称呼传统华人社团、以及“宗乡总会”成立等一系列事件的出现。自此以后,在建国后面对困境的宗乡社团被赋予传承中华语言文化与华族传统价值观的新使命,亦使华人宗乡文化在国家脉络下的生存与发展有了功能上的新定位。
第二、基于“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与“种族和谐”的国家政策,政府鼓励各种族民间社团主动承担维护国家种族宗教和谐的举措,不仅为华人社会在新时期的发展注入更多新内容,亦赋予华人宗乡文化承担与非华族文化交流的新功能,进而促使宗乡文化向作为国家文化组成部分的方向转型。
第三、宗乡社团是推动宗乡文化重振与发展的主要力量。伴随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在社会变迁新形势下的调整与转型,宗乡社团迎来发展的转机。进入新世纪以来,因应时空变迁与新加坡各项政策的影响,宗乡社团在运作内容与社会功能诸方面呈现出“凝聚、开放与融汇”等三个显著特征。这些变化不仅使宗乡社团逐渐摆脱建国前期被边缘化的困境,亦使宗乡社团能够更为自信地传承与发展包括宗乡文化在内的中华语言文化。这为宗乡文化的重振与拓展提供了组织与运作机制的保障。
(2)华人宗乡文化的当代演化
由于在新加坡建国后的二十年里华人社会文化基本陷于停滞状态,故本书重点考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华人宗乡文化。有鉴于当代重振宗乡文化的组织机构主要是宗乡社团、故本书也涉及宗乡社团在当代的变迁与转型的研究。
综合各类记录与笔者的田野考察,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进入一个重振与拓展的新时期。
先谈华人宗乡文化在当代的重振与复兴。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以涵盖祖籍地与移居地两方面内涵的宗乡文化为纽带,重建与拓展和祖籍地、区域以及海外华人宗乡社团的跨国经贸文化联系网络,进而提升与强化宗乡文化在新加坡社会的重要地位。这是重振华人宗乡文化的外部途径。
在新加坡内部,华人宗乡社团主要是透过唤起宗乡社群的历史记忆与中华文化认同来重振建构于殖民地时代的华人宗乡文化。
恢复中华传统节庆,是宗乡文化重振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节庆既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有效载体,亦凝聚与承载着炎黄子孙的民族与文化认同。当中华传统节庆伴随闽粤移民的南来而传播到新加坡后,不仅对保持殖民地时代华人社会的“中国化”起着决定作用,同时也为华南移民提供社群整合与凝聚的重要舞台。然而,由于新加坡在建国后的社会变迁,中华传统节庆文化在华人社会尤其在华人年青一代中已逐渐淡漠。
中华传统节庆在新加坡的复兴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时刚成立不久的宗乡总会经过对一千多个家庭所进行的调查,对华族传统节庆在华人社会衰落的严重状况深感忧虑。为此,总会在政府的支持下,展开一场复兴华人传统节庆习俗的大讨论,并出版中英双语的《华人礼俗节日手册》,用简单的语言与生动的彩色插图,让华社重新了解中华传统节庆文化的意义及其庆祝方式。该书在1989年10月15日由时任第二副总理的王鼎昌主持首发仪式。1990年11月11日,总会在第五届常年会员大会上,推出“春节、清明、端午、乞巧、中元、中秋、重阳、冬至”等八大节日彩旗。在华人传统节庆来临时,这些彩旗在机场、车站、街道、商店等处飘扬,由此在全社会掀起一股复兴中华传统节庆的热潮。
在新加坡中华传统节庆的复兴中,宗乡社团扮演重要的角色。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许多华人宗乡社团重新将清明、中秋、重阳、春节等华族节庆活动作为常年运作的内容。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从很多社团编撰的特刊、会讯等的记录看,传统节庆活动已在华人宗乡社团复兴并制度化。
在宗乡社团开风气的带动之下,春节、清明、中元、中秋、重阳、冬至等已经成为今天新加坡华人社会最重要的节庆活动。不仅如此,这些源自中国的传统节庆,有不少在内容、方式与规模等已呈现出许多具有新加坡在地与时代之特色。例如,“春到河畔迎新年”的新加坡春节庆典、“多元种族庆中元”、“多元种族庆中秋”、“多元种族捞鱼生”等跨种族的传统节庆活动、以及本书所考察与讨论的当代新加坡中元节等等。
进入二十一世纪,宗乡文化重振进入方言文化领域。
如前所述,在殖民地时代,脱离原乡发展轨迹的华南传统乡土民间文化,在为闽粤移民的社群重组与华人社会建构提供文化资源与组织原则的同时,其自身也伴随华人新家园在新加坡土地上的建立,从地域文化发展成为具有社群边界的华人宗乡文化。而建构宗乡文化的根基,即是传承自祖籍原乡的各社群的方言文化。然而,由于建国后的社会变迁,方言与方言文化陷入困境。尤其是1979年由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发起的“讲华语言运动”,虽然有助于华语在新加坡的推广,但其目的却是要“多讲华语,少讲方言”。在此社会大环境下,方言与方言文化更是每况愈下,与此相联系的“祖籍”概念、“祖籍认同”与 “宗乡社群认同”也随之逐渐淡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为了挽救新加坡华人方言文化,在政府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正在转型中的华人宗乡社团纷纷开办福建、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等方言学习班、举办以朗诵唐宋诗词为内容的方言诗词大汇演、以方言讲授中华文化与中国历史课程等。
二十一世纪以来,新加坡华人方言文化的重振有了新的内容与进展。一方面,作为各方言社群总机构的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南洋客属总会、广东会馆、海南会馆等纷纷联合属下会馆、同乡会、宗亲会等各社团,举办贯以社群符号的文化节,如“福建文化节”、“潮州文化节”、“客家文化节”、“广东文化节”、“海南文化节”等。这些由各方言社群举办的文化节,其所展演的内容非常丰富多彩,既有祖籍原乡的文化传承,亦有该社群在地的文化创造。到目前为止,新加坡这类文化节的举办仍方兴未艾,且已经呈现定期举办的制度化形态。另一方面,各方言社群纷纷举办各种文化活动,重振传承自祖籍地的南音、粤剧、国术、龙狮、客家山歌、潮州大锣鼓等民间文艺、民间音乐等、以及方言社群独特的民间信仰、节庆文化等内容。上述具有社群边界的文化形态的重振与运作,同时具有重新唤起与强调所属社群的历史记忆与中华文化认同之功能。
当代华人宗乡文化的拓展,主要涉及新加坡华人社会与非华族社群。
在现有教育体制外展开与中华语言文化相关的活动,是当代华人宗乡社团运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兴办华校、传承中华文化与维系华人的民族与文化认同,是殖民地时代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社团最重要的一项社会功能。面对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的社会变迁、华文教育体系终结、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承缺乏体制内教育制度的维系、华人年青一代对中华语言文化逐渐淡漠的现状,华人宗乡社团以发放各类奖助学金、举办从小学、中学到大专各个层次的华文作文竞赛、与大学及学术团体合作,推展各类与讲华语相关的“华语讲故事比赛”、“华语演讲公开赛”、“华语常识大赛”等诸多方式,努力为在新加坡保留与传承中华语言文化而艰难奋斗。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代华人宗乡社团更为积极地展开跨国会务,并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参与全球华人社团联谊性质的活动内容,逐渐转入跨国合作展开中华文化活动的新阶段,主要由宗乡社团推动的包括方言文化在内的中华语言文化活动,亦开始呈现出由新加坡本地向着跨国跨地区方向拓展的趋向。
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的发展还涉及非华族社群。
综合各项记录,在当代新加坡,华族与非华族的文化交流主要是透过同庆华人传统节庆与不同种族同台表演歌舞等形式。有关非华族参与中华传统节庆活动的报道,最早见诸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的新加坡华文报刊。进入新世纪以来,华族与非华族间互动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各类相关的资料显示,华族与非华族共庆端午、中元、中秋、重阳、春节等中华传统节庆、非华族参与福建会馆、中华总商会等开办的方言与华语学习班等项,正在成为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民众联络所、公民咨询委员会等社区基层组织制度化的运作内容之一。
除了传统节庆与歌舞表演,当代新加坡民间的种族文化交流已呈现出进入年轻世代的趋势。一个有价值的个案来自新加坡福州会馆。福州会馆自1995年开始每年举办 “全国小学现场华文作文比赛”, 2000年增设“非华族生优异奖项”。该奖项自设立以来的近二十年取得不菲成绩。在2017年举办的第二十三届大赛中,参与比赛的非华族获奖者已占获奖总人数的20%。
总之,近些年来有关非华族参与华族传统节庆、或不同宗教之间的友好关系等的报道,越来越多见诸于报刊和华人社团的各项记录,显示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理念已经开始深入到新加坡民间社会之层面。而就种族间交流的内容而言,宗乡文化无疑是促进华族与非华族互动与交流的一座重要桥梁,这不仅有助于非华族对华族的了解,客观上也促进中华语言文化在非华族中的传播。
综上所述,在新加坡建国之后的半个世纪,华人宗乡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建国前期,受制于政府政策与社会变迁,华人社会与宗乡文化面临生存困境的严峻挑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以来,伴随新加坡的转型,华人社会迎来发展契机,华人宗乡文化由此进入重振与复兴的演化进程。基于当代新加坡中华文化发展缺乏华文教育体系的维系,加上受社会变迁、世代交替等因素的制约,宗乡文化的前景还是充满挑战与艰辛。不过,当代宗乡文化在重振的进程中所显示的跨种族、跨国界的趋向与特点,有可能为宗乡文化的未来图像注入新发展动力。当宗乡文化跨越华族、成为非华族愿意了解或参与的华族文化内容,客观上强化了宗乡文化对于新加坡多元种族国家文化建构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宗乡文化的跨国特点,亦使其在新加坡本土以外的、包括亚细安区域、中国与大中华地区乃至海外华人社会等在内的世界有更大的拓展空间。不言而喻,当代华人宗乡文化重振与拓展,不仅有助于重新唤起包括宗乡社群在内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民族与文化认同感,亦有助于促进新加坡国家文化之建构。
03
华人社团档案与资料的文献及学术价值
本书研究的资料,主要来自华人社会文献、华文报刊报道、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在上述三类资料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献中有相当部分是笔者新近收集并首次运用于研究中。对这些文献的整理与解读,使笔者在研究视角与研究内容上有了与现有研究不同的思考。有鉴于此,在这一节笔者重点阐述本书所运用的华人社团档案、资料及这些文献的学术价值。
1、华人社团档案
一般说来,研究东南亚华人社会历史文化的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获取文献资料。其一为殖民政府或当地政府档案,其二为华人社会文献,包括不同类型的华人社团组织的章程、会议记录、名册、编撰的纪念特刊等各类记载。然而,在东南亚殖民地时代,由于殖民政府或当地政府没有建立规范而完整的华人档案系统,学者很难从官方档案中获得足够的研究资料。此外,由于这些官方档案 “大多都是表达一种局外人顺便观察一下华人社会的观点”,对于从内部研究华人社会历史的发展与演化具有局限性。有鉴于此,华人社会文献更显其重要性。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原因制约,华人社会在其历史演化进程中,亦基本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保存历史资料,更谈不上建立制度化的文献收藏与管理体系。许多记载华人社会发展历史的社团会议记录、账本等珍贵资料,不是毁于战火,就是伴随时光推移的社会变迁中被毁坏或遗失了。与东南亚大部分国家一样,从1819年开埠至今不到两个世纪的新加坡,保留下来的华人文献已经不多。特别是历经日据前后的战乱与战火,有关二战前华人社会的记录被大量销毁。1965年新加坡建国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快速的市区重建工程的推展等,再次造成各类华人社会文献的严重流失。因此,研究资料的匮乏,几乎是所有该领域学者面对的共同难题。
笔者在新加坡多年的工作与研究中,收集了一批华人社团档案。这批文献数量相当多,主要涉及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社会三类重要社团形态,即会馆与其所兴办的华文学校、帮群坟山与庙宇组织。这批华人社团档案,除了有学界已较为熟悉的章程、名册、董事部、同人大会的会议记录、征信录等外,还有两类新文献,一类是社团和华校的账本账册,另一类帮群坟山档案。
到目前为止,海内外学界在运用华人社团文献时,主要来自文字类议案簿、章程名册、金石碑铭、纪念特刊等记录。华人社团账本是东南亚华人社会文献中另一类以“数字”记录的重要文本。相较于文字类文献,华人社团账本具有计量学与统计学上的意义。透过账本所属社团对其在管理运作中所有往来账本系统、细致的登录,真实、具体且不间断地保留了账本所涉及年代华人社会内部的社群关系、认同形态、管理系统、运作方式等的记录。换言之,它是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不仅可为研究者提供可与碑铭、会议记录等互为映证的文献,亦因其记录的内容与方式具有真实、具体、细致、全面、连续等特点而能够给研究者以新资料,因而深具学术与史料价值。
就研究意义而言,华人社团账本具有为东南亚华人研究领域提供新视角与新内容的重要价值。到目前为止,海内外学界基于所运用碑铭、会议记录等华人社会文字类文献,主要是从政治、社会及文化等层面、即以一种社会文化视野考察殖民地时代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建构与历史演化。华人社团账本则是从华人社会经济史的视角考察东南亚华人社会最基本与最重要的文本记录。
本书以华人社团账本进行研究的一个个案,是作为新加坡嘉应五属社群总机构的应和会馆与其所兴办及管理的应新学校。笔者运用应和会馆与应新学校保留下来的“二战”前的账本账册、并结合会议记录、章程等文献,从华人社团经济的视角,具体考察建基于移民的“方言群认同”与“祖籍地缘认同”的应和会馆,如何在半自治的殖民地时代建立一个具有嘉应五属社群边界、且能承担维持该社群的运作与整合双重功能的财务系统。另一个个案是广惠肈、嘉应五属、丰永大三社群总机构海唇福德祠绿野亭。笔者细致爬梳与分类整理了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与属下社群的账本记录,从中探究南来的闽粤移民在运用源自华南乡土的民间信仰与坟山崇拜等文化资源的同时,亦透过经济层面的运作,来建构“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社群关系与“整合大群、凝聚小群”的认同形态,以解决这个跨方言与跨地缘的帮群组织的凝聚与整合问题。
另一类文献是华人帮群坟山组织的档案与资料。由于华人坟山内通常都建有福德祠等庙宇,所以保留下来的坟山资料中,通常也包括与庙宇管理相关的记录。这些坟山文献大致可分成文字类的死亡登记、埋葬记录、董事会、监事会、同人大会等的会议记录、章程与名册等、数字类的账本账册、以及金石碑铭等几大部分。金石碑铭又可分成记载坟山组织历史发展进程重大事件的碑文与坟山内社团总坟石碑碑文等两类。此外,还有坟山组织历年编撰的纪念特刊、超度先人的万缘盛会特刊等等。
在既有的东南亚华人研究学术成果中,学者多将关注点集中于“生者”的世界,注重研究会馆、宗亲会等社团组织。保留下来的华人坟山组织档案与资料显示,对东南亚华人社会而言,在“生者”的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与此相对应、且与神明相联系的 “死亡”的世界。有鉴于此,现有的仅从“生者”世界进行考察的研究取向与研究内容是不足够的。坟山组织档案与记录则为从一个“死亡”世界的视角考察与研究东南亚华人历史与社会文化提供了最基本与最重要的文本文献。
在本书中,笔者将收集到的广惠肈碧山亭与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两个坟山组织的档案、金石碑铭等各类文献,运用于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帮群社会建构的研究,具体考察与讨论闽粤移民如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祖先崇拜”与“坟山崇拜”、透过对移民先人丧葬与祭祀的处理来凝聚“生者”的社群认同与整合的问题。而伴随这一进程,源自华南原乡的祖先崇拜也向着虚拟血缘与泛血缘的方向扩大,发展出社群化的祖先崇拜之形态。
2、华人社团资料
华人社团资料,是另一类重要的华人社会文献。
编撰与出版纪念特刊,是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一项重要传统。对各类华人宗乡社团而言,纪念特刊的编撰,是其从殖民地时代延续至今的重要运作内容之一。笔者认为,对缺乏档案记录系统的东南亚华人社团而言,纪念特刊是华人社会书写与记载自身历史的文本,深具文献价值。因此,本书注重对华人社团特刊的收集与运用。
除了社团特刊,本书运用的华人社团资料,还包括目前学术界关注不多的社团“会讯”。
从笔者收集到的资料看,保留下来的新加坡建国前的华人社团会讯并不多见。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将编撰与刊发“会讯”作为一项会务内容,大致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例如,宗乡总会会刊《源》始刊于1986年、福建会馆会讯《传灯》于1992年创刊、广惠肈碧山亭于1997年创刊会讯《扬》、福州会馆在1993年复刊创办于1959年的会讯《三山通讯》、并将其改名为《三山季刊》等等。自世纪之交到新世纪以来的近二十年,伴随在新加坡内外时空情境变迁下华人宗乡社团的转型与重振、运作内容与社会功能的改变等等,从宗乡总会、中华总商会到福建、潮州、广府、客家、海南、广西、三江、福莆仙等各方言社群的会馆、宗亲会、庙宇、坟山、俱乐部等各类社团纷纷编撰发行“会讯”“会刊”。这些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会讯”“会刊”,其所涉及的华人社团之多、数量之大,正在成为研究当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一类重要资料。
“纪念特刊”与“会讯”虽同为华人宗乡社团所编撰,但相较于内容广泛、篇幅较大、编撰与发行周期较长、出版时间不确定的纪念特刊,当代“社团会讯”则具有定期、制度化、纪实、持续且不间断的编撰与刊行方式。在内容上, “会讯”主要涉及当下三个月、半年或一年所属社团的会务与运作状况,故“会讯”的篇幅通常都不大,少则几页,多则十数页,编撰与发行成本远低于社团特刊。这些不同于社团纪念特刊的文本与刊行特点,使作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新加坡社会变迁产物的 “会讯”,能够真实、具体、动态地记录与展示华人社会尤其是宗乡社团与宗乡文化的当代图像,显示“会讯”“会刊”具当代特色的文献价值。有鉴于此,笔者对华人社会文献的收集,除了关注华人社团特刊这类学界已较为熟悉的文本外,尤其重视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方崭露头角的各类社团会讯及会刊,将其运用于本书有关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当代转型与华人宗乡文化重振的具体考察与研究中。
综上所述,笔者对新加坡华人社团档案与资料的收集、整理与解读,使笔者在对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社会文化的考察中有新的学术视角、探究内容与一些不同于现有研究的思考。
04
结语与讨论
本书以中国与东南亚等多元的研究视角,主要运用会馆、华校、庙宇、坟山等社团的碑铭、议案簿、章程、名册、账本账册、死亡登记、埋葬记录、纪念特刊、会讯等新加坡华人社会档案与资料、田野调查的口述访谈与华文报刊报道等各类文献、结合宏观考察与个案研究,重点探究自1819年新加坡开埠之后、脱离闽粤移民祖籍原乡发展轨迹的华南地域传统民间乡土文化,如何在新加坡从殖民地时代到本土社会的时空变迁脉络下、伴随华人社会的建构与演化而发展成为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从华南地域文化发展成为新加坡华人的社群文化,是殖民地时代华人宗乡文化建构的基本内容。而在新加坡建国以来半个世纪时空变迁的脉络下,当代华人宗乡文化正在经历重振的艰难挑战。与此同时,具有华人社群边界的宗乡文化,也呈现出朝向新加坡国家文化建构轨迹演进的发展趋势。
作为源自文化移植而在新土地的时空脉络下创造性发展的产物,笔者期盼本书对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的研究,有助于对以下三个课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与探究。
其一、中华文化体系的海外发展
众所周知,作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中华文化体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进程。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整合与凝聚了华夏大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各个不同民族与不同的文化形态,创造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与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亦将这一文明形态传播的世界各地。相关的研究显示,中国人与海外的交往,至少从先秦两汉即已开始。在此后的近二千年里,随着中国与世界经贸文化联系的不断扩展与加深,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学、音乐、戏剧、宗教、中医药等也传播到世界各地。就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而言,今天的东南亚无疑是最重要的地区之一。秦以前中国与该地区已有生产与文化交流。秦汉以降,民间与官方可经海路或陆路抵达东南亚。宋元以后,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在政治、经贸、移民、文化等诸多领域展开。十五世纪初,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多次经过东南亚地区。从宋元到明清,中国华南社会经济变迁,海外贸易迅速兴起,东南亚成为中国展开海外商贸交易的重要与主要地区。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陶瓷之路,其所经之处皆主要在该地区。在中国与东南亚政治经贸文化交流不断扩展的同时,南来的中国人不断增加。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年,大量华南移民来此拓荒,不仅为东南亚的大开发提供了劳动力资源,也将中华文化传播到这片土地上。
由以上阐述可见,中华文明体系的形成,包括华夏大地与海外的两种途径。然而,到目前为止的有关中华文化海外发展的研究,主要还是从文化传播的视角进行考察。对于海外炎黄子孙如何在不同于祖籍国时空脉络的世界各地创造性地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较为深入的研究与相关的成果积累还不是太多。
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在地视角考察中华文化的海外发展。本书的研究显示,作为外来的文化形态,经由各种途径、尤其是伴随中国移民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并非仅只是简单的移植与空间上的延伸,而是在当地新时空脉络下的传承与创造,并逐渐发展成为所在地区与国家的中华文化。在海外发展的中华文化与五千年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且丰富与发展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其自身也构成中华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是中华文化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总之,笔者认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体系,即是中华民族在华夏大地的创造,亦有海外的炎黄子孙与热爱中华文化者对其发展的贡献。本书期盼透过对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建构与演化历史进程的具体考察,为研究中华文化的海外发展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个案。
其二、从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移植与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建构反思“大小传统”的理论框架
本书关注与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以新加坡华人社会为研究个案,考察近现代伴随华南移民而移植到东南亚的中国传统民间文化,对于该区域华人社会建构与演化的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从中国传播到东南亚的中华文化,主要是华南的传统民间文化形态。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受制于近现代中国到东南亚的华南移民构成。虽然现有的文献记录与考古发现显示,华南人来到东南亚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不过大规模的闽粤移民南来拓荒还是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年。在中国近现代一波接一波的移民浪潮中南来的闽粤拓荒者中,绝大多数是穷苦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中的许多人完全没有或仅受过粗浅的教育,更不用说接受儒家精英文化的熏陶。这样的移民构成,使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文化呈现出主要源自华南地域传统民间乡土文化的基本特点。
移植而来的华南地域传统民间乡土文化,以“宗”、“乡”所蕴含的地域与血缘为核心、涵盖祖先崇拜、民间信仰、方言习俗、传统节庆等诸多内容。在半自治的新加坡殖民地时代,这些脱离原乡发展轨迹的华南民间乡土文化承担新的历史使命,为闽粤移民在这片新土地上重建家园提供文化资源与组织原则,其自身则伴随华人社会建构的历史进程,从华南地域文化发展成为具有社群边界的华人宗乡文化。当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从殖民地时代进入本土社会,华人社会随之转变身份认同,进入新兴国家的发展脉络。然而,建国后新加坡国家认同建构的道路并不平坦,致使华人社会和中华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乃至生危机。当社会变迁诸因素为华人社会文化迎来发展契机之时,传承自华南的宗乡文化再次承担历史重任,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以来新加坡中华文化重振的主要内容与形态。与此同时,在政府推行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国策鼓励之下,华人社会为促进国家的种族和谐,透过宗乡文化与非华族展开文化交流,从而使宗乡文化具有让马来、印度等非华族了解与认识中华文化与华人习俗的新功能。
本书的研究,希望有助于学界了解中国传统民间文化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与东南亚华人社会建构与演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意义,进而重视与该课题相关的研究。另一方面,对传承自华南地域传统乡土文化的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的研究,也促使笔者思考,现有的关于中华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区分,是否适用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文化?
我们知道,大传统和小传统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墨西哥乡村地区时提出的。该理论对人类学、社会学、史学、哲学等诸多人文学科均有相当大的影响。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客观上存在经典与民间的区别,所以大、小传统是学者对中国社会文化进行分层研究时常加以运用的一种理论框架。例如人类学家李亦园批评杜维明仅从“大传统”即士大夫精致文化概念去诠释“文化中国”,他认为还应该有“民间文化”即小传统的层面、以及精致文化与民间文化互动的视角。为此,李亦园以大小传统理论为切入点,提出沟连中国文化中大传统两部分的“三层次均衡和谐”的理论模式,试图通过抓住两个传统之间的共性或相通之处,来把握中国文化的特性。
那么当中华文化以各种途径、尤其是透过移民而传播和移植到东南亚、并在当地时空脉络下历经再建构与演化的进程之后,大小传统的理论框架是否还能适用于对东南亚中华文化的研究?
本书的研究显示,虽然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的源头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华南地域民间乡土文化,但当该文化形态脱离原乡之后已转变发展轨迹,承担为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华人社会建构提供文化资源与组织原则的新历史使命。而在英殖民政府统治下的移民时代,虽然以会馆办学为主体的华文教育在新加坡蓬勃发展,但华人社会始终没有出现类似中国本土的大传统精英文化层。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海外第一所以中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南洋大学的创办,原本有可能促进新加坡中华文化发展并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但遗憾的是,当新加坡在1965年建国后,基于种种内外挑战与社会变迁,最终因南洋大学合并(关闭)与华文教育体系的终结而打断这一进程。在以上两个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下,传承自华南、在新加坡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时空脉络下建构与演化的宗乡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的主流形态。事实上,从本书对华人宗乡文化当代图像的考察显示,在今天的新加坡,宗乡社团是保留与承传中华语言文化的重要力量,宗乡文化不仅是华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透过华人宗乡社团的运作,已成为新加坡不同种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客观上促进中华语言文化与传统节庆习俗在非华族中传播。
以上所述,无疑说明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并非仅仅是空间上的简单延伸与移植,而是在当地时空情境下的传承与创造性的发展,进而也促使我们思考,是否应该从跨越大小传统的视角来研究东南亚华人文化。本书对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建构与演化的研究,似可提供一个对此问题进行反思的个案。
其三、东南亚中华文化的双重特征与当代价值
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华文化体系与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海外中华文化的关系,存在以下几种看法。一种是将二者等同。此种认知较为流行于中国学界的一些研究者。另一种是将二者割裂与分离。例如,上世纪末马来西亚关于马华文学脱离中国文坛的“断奶”论争。本世纪初在美国学界出现的将中国大陆文学排除在外、自成一系的“华语语系文学”等。
在以上两种认知之外,杜维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提出“文化中国”的理论,并以“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海外各地侨居的华人”、“学者、自由作家、记者”等三个象征世界的实体来表述。李亦园则从小传统 “民间文化”的层面、强调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互动,对杜维明“文化中国”理论进行补充。本世纪初,郭振羽重新审视杜维明的“文化中国”理论,认为“中国”二字容易造成对政治实体与国家疆界的想象,故提出“文化中华”概念。他指出“流播五洋七洲”的中华文化与华夏大地的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并强调“文化中华”在现今世界的存在,显示华夏文化所具有的开放、多元与包容之特质。以上几位学术前辈所提出的“文化中国”或“文化中华”,其特点是试图在跨越政治与国家等疆界的前提下,将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海外中华文化纳入中华文化体系之内。
针对上述几种看法与论述,本书从对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研究,提出东南亚中华文化具有双重性特征的观点。
本书认为,从一个文化体系在具体时空与社会变迁的脉络中传承与发展的视角,东南亚中华文化与五千年华夏文明一脉相承,是中华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本书所讨论的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其所涉及的华语、华文、闽粤方言、祖先崇拜、神明信仰、节庆习俗、南音、粤剧、客家山歌、舞狮等诸多内容,均属于中华文化之范畴。近年有关新加坡各种族身份认同感的调查亦证实,中华语言文化对于新加坡华人华族身份认同感的重要意义。根据这项调查,在一千多位华族受访者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认为,“讲简单华语、庆祝农历新年与使用华语”,是在文化上确认其华族身份与文化属性的最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本书亦认为,在东南亚时空情境下传承的中华文化也发展出具有在地特色的内容与形态,并伴随华人社会在二战后身份认同的转变而落地生根,成为所在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本书所研究的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的建构与演化进程为例。宗乡文化是闽粤移民在新加坡半自治的殖民地时代、为适应家园重建的需求而创造性地传承华南传统民间文化的产物。而在新加坡独立之后,宗乡文化的演化轨迹又与新兴国家发展脉络下的华人社会转型、多元种族的国家认同与国家文化建构等进程密切相连。因此,历经新加坡从殖民地时代到建国之后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传承自华南的华人宗乡文化不仅发展出具有在地特色的内容与形态,其自身则在事实上成为新加坡国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上述现象并不仅存在于新加坡。以马来西亚为例,从潮州民俗发展成为新山华人五帮共庆的神人嘉年华“柔佛古庙游神文化”、享誉大中华的二十四节令鼓、兼具文化传承的“传灯”与社区共庆等多重功能的中秋园游会等,都是马来西亚华人运用传承自华南传统民间文化中的神明信仰、节庆习俗等资源、在当地时空情境下的文化创造。这些文化形态无疑与中华文化体系一脉相承,同时也具有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之特色。
东南亚中华文化的双重特征,在当代具有重要的价值。东南亚中华文化与中华文化体系一脉相承,充分显示中华文化体系的开放、多元、包容与适应时空环境顽强发展的强大内在生命力。在东南亚,中华文化的双重性特征,使其能在该区域承担多元的社会功能。东南亚的中华文化,是维系本区域内不同国家的华人社会、中国大陆、港澳台以及世界各地华人社会的一条重要的文化纽带。而对于东南亚各国的华人与华人社会而言,在与其他种族拥有共同的国家认同之下,中华文化则是他们强化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基石与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在提倡多元文化、种族和谐的那些东南亚国家,例如新加坡,中华文化还具有让马来、印度等种族了解华族与华族民间习俗等重要功能。这不仅可以促进东南亚的种族和谐、华人与非华族的友好相处,亦有助于推进华人社会与中华文化在该区域的发展。
综上所述,笔者阐述了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并就东南亚中华文化研究提出一些思考。行文至此,笔者还需指出,虽然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基于内外因素与政府政策的改变,新加坡华人社会迎来发展契机,华人宗乡文化亦开始逐渐重振与复兴,但仍面临来自内部与外部世界的诸多制约与挑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就当代新加坡华人社会与中华文化的发展前景而言,其最大障碍是新加坡教育制度的改变、中华文化失去华文教育体系的维系与支撑、以及随之而来的、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华人新世代对民族文化认同与祖籍认同感的淡化。与此相联系的,是作为宗乡文化发展主要推动力的宗乡社团难以获得华族年轻世代的认同。另一方面自中国改革开放相继来到新加坡求学、工作或定居的人数众多的中国新移民,对新加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注入许多新因素。这些新因素在有助于增强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感与促进中华语言文化在新加坡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不少社会问题。
在外部,除了不断变化中的世界局势与亚细安地缘政治形态,中国是影响未来新加坡与华人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刘宏指出,新加坡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新加坡也是海外人民币最大的离岸市场。除了经贸关系之外,中国对新加坡而言,还不仅仅是个国家、而是一种文化与文明,尤其是会被“内化”成为影响新加坡发展的很重要的因素。笔者很认同刘宏的看法。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的拓展、中国综合国力与中华文化在世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新经贸文化联系的扩大、新加坡华人与祖籍国、区域乃至全球华人关系的加强等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内化”成为影响与制约未来新加坡政府内政外交的制定,包括对华人社会文化的政策、新加坡社会经济发展、华人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以及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前景等课题的重要因素。
面对上述未来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正如本书所强调的,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的建构与演化是一个历史进程。伴随未来时空环境的改变,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而又作为新加坡文化组成部分的华人宗乡文化还会不断演化,并呈现出与那一时代相适应的新形态。
(本文为曾玲教授《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研究》一书的“绪论”,
第1-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
马来西亚研究资讯Informasi Pengajian Malaysia 爱生活@爱大马
 最及时的大马学术信息长按,识别二维码,加关注
最及时的大马学术信息长按,识别二维码,加关注
